戏曲文化:中华文明的艺术奇葩
前言:它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历经上千年生生不息;它曾是亿万人的感性生活的寄托与情感的沉醉之所,积淀着中国人的根和魂;在它那里,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得到最全面、最形象、最精美的体现。第一次赋予它“戏曲”概念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藉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宋元戏曲考》)

禹县(今禹州)白沙一号宋墓乐舞壁画

开封陕甘会馆戏楼

安阳金墓戏俑和舞台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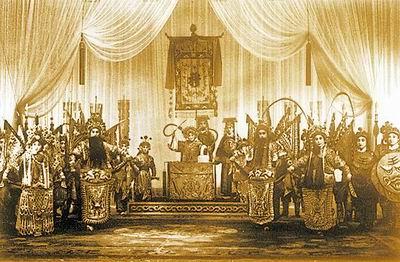

毛主席接见《朝阳沟》剧组成员
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照耀到中原,戏曲艺术就在这光照中萌芽。戏曲起源于河南,形成于河南,如今繁盛于河南,并从整体上影响着中国戏曲的创作与发展;中原戏曲种类之多、密度之广,全国少见。河南人爱看戏,爱哼梆子腔;戏曲是河南人与生俱有的精神基因,是河南人的生活方式。弘扬戏曲文化,正是为我们自己寻找一个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海德格尔曾说过:“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和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展开戏曲文化寻根之旅吧。
中原戏曲具有起源早、种类多、受众广、影响大等特点。“诸宫调”创始于开封,标志着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开始成熟的《目连救母》搬演于开封,北宋的杂剧也形成于开封。这些都表明中原是中国戏曲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戏曲来源于生活,扎根于民众,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戏曲源头在中原
作为世界戏剧史上独一无二的戏剧样式,中国戏曲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迟缓而漫长。它不似古希腊戏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登上人类文化的高峰,令千秋万世瞻仰遥想,却如涓涓细流绵亘久远,历经千载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原始巫术用歌舞娱神,到夏商宫廷俳优以表演娱人,到汉魏角抵百戏,隋唐参军戏,直到宋杂剧、金元本,多元血统使得它厚积薄发,大器晚成。
戏曲起源与中国古代乐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的河南,从远古时代就有了人类居住生息,他们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可以说,随着中华民族的先祖在中原这块大地上劳动生息,音乐歌舞也就相伴而生了。此后,20多个朝代在中原大地建都,催发了戏曲艺术的长期繁盛。中国戏曲从起源到形成,都离不开中原大地的滋养。可以说,中国戏曲之根在中州。
姚金成(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东方艺术》主编):有人说,河南戏曲之起源,应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郑卫之乡”,溱洧唱和为其滥觞。民国时期的王培义据孟子“河西善讴”(河指淇河,今河南鹤壁)的记载,得出了“‘河南讴’之起始远在尧舜之时,即晚亦生自战国”的结论。其实,河南这块土地上的艺术萌芽比这还要早。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七孔骨笛,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犹能吹奏出动人的旋律。安阳殷墟出土的3500年前的刻有鼓、龠、舞的甲骨文,表明当时的音乐歌舞已达到相当水平;禹县(今禹州)出土的周代巫傩青铜面具,则无疑是戏曲脸谱的上古先祖。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已经是令人向往的歌舞圣地了。《诗经·宛丘》中宛丘山下那“坎击其鼓”、“无冬无夏”的民间狂欢,魏文侯“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的痴迷,都让我们无法不去想象当时中原大地笙歌嘹亮、歌舞盈日的盛况。
两汉是“百戏”领风骚的朝代,作为东汉京都的洛阳,其歌舞戏剧之盛不言而喻。河南新密汉墓出土的“宴饮百戏壁画”,洛阳出土的歌舞百戏陶俑,南阳出土的达百块之多的有关歌舞百戏场面的汉代画像砖等,都足以表明当时河南戏剧的普遍繁荣。而《北齐书》、《教坊记》、《通典》等多部史籍中记载的产生于隋末河内(今沁阳),广泛流行于唐代的《踏谣娘》,不仅有了人物性格、角色装扮、舞蹈动作,而且有了独唱、帮腔,已经使用了“代言体”手法。
韩德英(河南省戏剧史研究专家):中原戏曲起源可追溯到夏启时代。夏代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已有“求倡侏儒,而为奇伟之戏”(宋·高承《事物纪原》)的记载。更值得一提的是,“诸宫调”创始于北宋都城汴梁(开封)。诸宫调是由多种宫调组合成的—个完整的长曲,元杂剧的形成直接受诸宫调影响。宋代王灼的《碧鸡漫志》记载:“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颂之。”《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一节记载:“诸宫调本京师(开封)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
而当时汴梁最有影响和深得观众欢迎的节目,要数瓦舍勾栏艺人们演出的杂剧《目连救母》。《东京梦华录》记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这是一个有相当高艺术水平的连台戏,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标志着戏曲的形成。从已出土的戏曲文物中,也可以说明宋代杂剧的昌兴和普遍流行,如1949年以来先后出土的有荥阳宋墓石棺杂剧图、偃师宋墓杂剧雕砖、禹县(今禹州)宋墓杂剧雕砖、温县宋杂剧雕砖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杂剧演员一般四人或五人,伴奏乐队多者五至七人,少者二人作演艺状。
郑传寅(武汉大学古典戏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继承宋杂剧、金院本、南戏和说唱艺术等成果的基础上,元杂剧出现。它标志着戏曲艺术的真正成熟。在灿若群星的元杂剧作家群中,“豫省亦颇不乏”(王培义语)有名的大家。知名的河南籍作家有郑廷玉、李好古、姚守中、赵文殷、赵天锡、陆显之、宫天挺、钟嗣成等。
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就生于汴京(今河南开封);著名剧作家李好古是西平路(今河南西平县)人。他写过杂剧3种。《录鬼簿》吊词说:“芳名纸上百年图,锦绣胸中万卷书,标题尘外三生簿。《镇凶宅》赵太祖。《劈华山》用功夫。《煮全海》张生故。撰文李好古,暮景桑榆。”还说他博学能文,腹内有万卷诗书,所作文字足以流传后世。《张生煮海》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杂剧。这出神话剧具有强烈的反抗封建统治的色彩,受到广大群众喜爱。《太和正音普》评说:“李好古之词,如孤松挂月,清秀优美,磊落不凡。”写出《看钱奴》的郑廷玉是彰德(今河南安阳市)人,他曾作杂剧23种,现存者6种。钟嗣成《录鬼簿》把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类,名次排在关汉卿、高文秀之后,位居第三。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其词“如佩玉鸣銮”。郑廷玉熟悉社会生活,洞察人情世态,作品题材广泛,对元代的社会生活、市井百态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描摹和反映,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被钟嗣成在《录鬼簿》置于“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之首的宫天挺是开州(今河南濮阳)人,他的杂剧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元代一大家,与关汉卿、马致远、乔吉齐名;而写下传世之作《录鬼簿》的钟嗣成是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他在这部著作中记录了元代152位曲家的生平及其著作,为后世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其书体例,也有开创意义,在后世学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河南的“中州调”,也是杂剧重要的腔系之一。
范红娟(中国古典戏曲博士、郑州师专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明代河南民间戏曲演唱活动十分活跃,乡村“春祈秋报”赛会活动多用戏曲。明后期,除了昆、弋、弦索等广泛流行外,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区,兴起了俗曲、小调,如“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泥捏人”“鞋打卦”等。不仅一般平民百姓喜爱传唱,就是文人墨客街市闻之,也赞赏不已,称这些“出诸里巷妇女之口”的小曲,为“时词中状元也”。(明·李开仙《词谑》)这些俗曲、小调,为河南地方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时,朱元璋之孙、周定王长子朱有瞛在开封写出了《诚斋乐府》,收有31种杂剧,明·沈德符称其“稳惬流利,犹有金元风范。”明代河南还有一些传奇作家,如李先芳、卢楠、桑绍良、李雨商等。睢州(今河南睢县)文人赵陛对,也“尝为乐府小剧,以寄其愤”,影响颇大。
清代河南也出现了一些杂剧、传奇作家,比如陈天清、王髄、吕履恒、吕公溥、李树谷等。吕履恒,字元素,河南新安人。康熙甲戌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是康熙年间著名诗人、剧作家、方志学家。撰有传奇4种,今存《洛神庙》一种,是现存最早的豫西调剧本。此剧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曾于杭州、宣化、湖南长沙等数地搬演。履恒工诗,著有《梦月岩诗集》20卷。时人王阮亭曰:“《梦月岩》诗高浑超诣,正以不甚似杜为佳。”;吕公溥是吕履恒之孙,主持荆山书院多年,著有《寸田诗草》,袁枚为之序,称其为“诗中雄伯”。作为当时著名剧作家,他有杂剧《弥勒笑》传世。该剧是根据张漱石的《梦中缘》改编成的梆子戏剧本,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明后期至清康乾时代,地方戏在“花雅之争”的铿锵锣鼓中纷纷登场亮相。弦索腔、锣戏、卷戏、梆子戏和昆曲、徽剧等数十个剧种,在中原大地争奇斗艳。当今河南流行的主要剧种和稀有剧种,或萌芽,或形成,或成熟,都在这一时期。
马紫晨(河南省著名戏曲史专家、民俗专家):仅从明万历之后的400余年间,先后在河南境内产生、存在或流行过的各类戏剧品种即有近80个,其中戏曲剧种60多个,最终形成了以豫剧、曲剧、越调为主体,大平调、大弦戏、宛梆、道情、二夹弦、怀梆、四平调、蒲剧、豫南花鼓戏等多种剧种百花齐放的戏曲体系。目前,河南尚有35个剧种在活动或残留踪迹可查;16个剧种有专业剧团演出。2006年第一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是豫剧、曲剧、越调等10个剧种;2007年2月,进入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除前述外,又有二夹弦、落腔、花鼓戏等12个剧种。其品种、数量均居全国各省前列。尤其是享誉神州的豫剧,从1984年起,在全国的专业剧团数量即达239个,流行区域则有22个省(市、区),包括上座率、经济自给率、从业人数和观众覆盖面等在内,当今的豫剧确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最大的地方戏品种。而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河南曲剧,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依其专业演出团体数量而名列全国365个剧种的第9位。
石磊(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理论家、剧作家):说豫剧是全国性的大剧种,一点也不夸张。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山西、河北、湖北、安徽、新疆、江苏、山东甚至西藏、贵州、四川等20多个省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团。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大的文化气候影响,豫剧的分布区域虽然有所萎缩,但其分布区域之广,专业剧团之多,观众覆盖面之广,目前在众多的地方戏家族中仍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就连宝岛台湾也活跃着一支国光剧团豫剧队。豫剧,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远离其生存母体,而能在对她来说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的台湾省存活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它不仅没有消亡、衰败,而且壮大发展,演遍了全宝岛,并于1997年演到世界三大洲的17个国家,这种奇特的艺术现象,在我国300余个地方剧种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豫剧独有的骄傲,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现在正在梳理有关《海峡两岸豫剧艺术交流的历史与现状》的课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查阅到了不少的资料,其中有关台湾戏剧与中原戏剧与文化血缘关系的论述。比如作为台湾本土生成最古老的戏剧形式——南管、傀儡、皮影,此三者均源自宋代。特别是南管这种戏曲样式,从其曲牌结构、套曲结构、管门板眼以及乐器形制、乐队建制等,均与宋大曲有相似之处。而像傀儡、皮影戏,则是早年盛行于古都汴京的戏剧形式,宋室南迁时,随大批中原士族带入闽南,而最后辗转入台。台湾的古老剧种之一北管,与北曲杂剧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均属包括郑、汴、洛三大古都在内的中原音韵之正声。所以,在台湾戏曲史研究方面具权威性的学者、台湾大学的客座教授曾永义先生曾经说:“在台湾早期农业社会里深受欢迎的南管、傀儡、皮影及北管,若追本溯源,都和河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
——中原戏曲以质朴自然取胜
“黄土厚,黄土黄,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诞生于中原大地的戏曲艺术,带着天生的民间性格,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无论是豫剧的激昂豪放、曲剧的清新柔美还是越调的苍劲沉雄,都渗透着中原人的群体性格,都关照着普通百姓的好恶爱恨,是世世代代中原人民审美心理沉淀的结晶。那一台台在全国赢得如潮好评的剧目,那如火如荼的戏迷演唱活动,那遍地开花的戏曲茶楼,那备受关注的“梨园春现象”,共同构成了河南戏曲文化的独特景观。
魏明伦(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著名剧作家):不得不承认,在当今中国地方戏市场中,豫剧是个特殊的个案,不但在河南,而且在全国都有着广泛的市场。豫剧为什么在中国戏曲、中国戏剧甚至中国舞台剧陷入“台上热闹,台下冷清”这么一种现状的时候,还能有那么多以农民为主的观众?大概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河南戏曲与生俱来的草根性,如此家常,如此世俗,如此与生活不可分,那种热爱是骨子里的。我们一般认为豫剧很“土”,但那种土是一种大俗大雅。如果河南戏曲一直扎根民众,则未来生命力很强。
郑传寅:豫剧生机蓬勃,活力无限,信手拈来尽是自然口语,寻常琐事,沁人心脾。激动处掏肝剖肺痛快淋漓,深情处细说情真意笃。说它土,土得可爱,令人想紧紧拥抱,说它俗,却一点不空泛。豫剧的剧场规律不如京剧严谨,但是也因此不像京剧会受惯性套式拘束。我以为,豫剧的艺术不在于情节题材的花样翻新,观众要听的是最原始、最贴心的感情。
姚金成:河南人,因其性格开朗豪爽,故表达情感酣畅淋漓,大喜大悲,敢爱敢恨;因其固守“仁义礼信”的道德标准,故崇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戏剧结局。如《卷席筒》中苍娃的母亲做了坏事,连亲生儿子也不原谅她,而且还去替无辜的嫂嫂坐监。河南这块土地,因其文化底蕴深厚,其民间语言犹如经过千熬百煮的浓汤浓汁,朴素、凝练、准确、生动。河南戏,因把握住了平正畅达的民众心理,故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情感认同和“疯狂般地拥护”。无论是苦难年代还是太平岁月,在戏台与看台这块天地里,永远是骚动的海、欢乐的洋。对拥挤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里是他们精神的圣土、欢乐的殿堂,他们对戏曲有着近乎虔诚的热爱和依恋。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历了长期灾荒、战乱、贫穷的河南人,依然能够保持乐观、坚忍、豁达的性格,因为他们在和自己血脉相连的戏曲中,找到了排解苦难、纾解愤懑、寄托情感、寻找快乐的途径。有如此“贴心”的戏曲伴随,再苦的日子也是甜的。
纪慧玲(媒体资深戏剧记者):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知道豫剧,第一次听到河南梆子的声音,王海玲一身喜红,摇摇晃晃坐在大花轿里活泼利落的形象还深印我脑海。我以为河南戏地方味儿就是这么足,这么地道,这么独树一帜。
戏剧学者汪其楣特别翻查了早期看戏笔记,温习当年回忆,还是觉得,即使同一戏码,比如《白蛇传》、《金水桥》、《奇双会》,豫剧的诠释都比京剧好。我主观认为,河南戏有浓厚的乡土味,生活气息,一直就是这个味道吸引人,让她与京剧一板一眼、大义凛然的气味不同。
范红娟:我的感觉,中原戏曲对中国戏曲最大的影响在于中原戏曲的世俗性,它影响着中国戏曲的基本品格和发展流变的基本走向。宋杂剧伴随着市井的喧嚣而繁盛。勾栏演出使中国戏曲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产生了商业化的戏曲演员,戏曲演员脱离了皇室贵族的豢养而和市民观众建立起一种商业性的经济依存关系。它导致戏曲走下神坛、迈出宫廷,走向市井民间。此后,世俗性一直成为中国戏曲的主流品格。即使是被称为“大雅之音”,常在小庭深院中演出的昆曲,也一样由于其叙事性和传奇性而被涂抹上一层俗世的油彩,这不能不说是来自于中原文化传统的哺育。至于各类地方戏曲词的俗俚化、音乐的民歌化、表演的身段化,无一不承袭着中原文化的世俗性色彩。
石磊:大凡一个民族艺术品种的诞生,与它植根于这个民族群体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地理环境之上的群体意识、群体性格、习惯,特别是民族群体的文化,包括心理结构和审美心理定势,有直接关系,蕴藏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现在,面对大的社会环境,戏曲艺术的走势趋于瓶颈,一些人的视线,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视线淡出了这一艺术品种,但这完全不代表它真正价值的消失。尤其是我们河南地方戏(包括一些稀有剧种),它所富含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它所具备的审美价值是其他包括号称“国粹”的京剧艺术在内的诸多地方性剧种所不能代替的。面对着这样厚重的河南戏曲文化资产,如何去保护、保存、传播、开掘和发展,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戏曲艺术工作者眼前的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艺术“同化”现象,人们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如何正确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适应、去发现,而不是去扭转戏曲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如何使作为艺术商品的戏曲艺术根据它自身在文化市场的运作中所得到的种种信息反馈去调节、完善、革新自己原有的步伐;既使这些祖宗留给我们后人的珍贵遗产保存完美无损,又不使其沦为博物馆藏品,这是积自上世纪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运动至今的近一百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是人们在今后的戏曲改革工作中首先应该严肃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用口来醒事
拿戈去惊人
——关注现实、惩恶扬善的中原戏曲基调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明代高则成《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而河南由于长期以来久居全国的政治中心,加上儒家哲学中重政治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因而造就了中原戏曲自觉的政治意识、时代意识、社会意识、责任意识。在贴近现实、惩恶扬善这一点上,中原戏曲显得坚决彻底。尤其是豫剧长期以来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调,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唱红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影响波及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世界。三国、包公、杨家将、岳家将等历史故事被改编为中原戏曲优秀剧目后,久演不衰,成为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贵财富。
杨兰春(著名剧作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朝阳沟》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七天里连写带排就上演了?”我觉得跟我在登封市大冶镇曹村一带的生活经历有关系。1945年,战争时期,我在那儿亲眼看见当地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更看到他们与八路军的鱼水深情和血肉关系。1957年,再次回到曹村,和老乡们朝夕相处。当地有老农民对我说:“老杨,你说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念两天书,谁家的姑娘不上几天学?读两天书上两天学都不想种地了,这地叫谁种呢?哪能把脖子扎起来?”我觉得农民说出了一个真理。那时正是党号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抓住了这个主题:城市知识青年王银环下乡与劳动人民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什么在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写出的《朝阳沟》到今天还有生命力?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从写人物出发,用唱词来表现各个人物的真实情感,刻画出有性格、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因为贴近生活,所以容易为观众接受。
石磊:说到中原戏曲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我想以樊粹庭的戏为例说明。中原戏曲经历了三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戏由乡村草台向城市剧院扩展,一批知识分子进入戏曲领域,对梆剧艺术品位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樊粹庭为陈素真创作的《凌云志》、《义烈风》、《三拂袖》、《柳绿云》、《萧壤恨》、《涤耻血》、《女贞花》等剧。作为河南近代戏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樊粹庭用眼睛观察生活,用笔反映生活,在其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具有我们中华民族心理特征、性格特征和民族气质的人物。他一生创作剧本60余部,人称“樊戏”。由于他关注社会,关注时代,故其剧目多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多反映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由于他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对女性心怀同情悯恤之心,故多描写受压迫、受污辱最甚的中国古代妇女;由于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故其剧作近贴时代脉搏。“樊戏”是最底层的艺术,是愤怒的艺术,更是时代的艺术。不同时期的河南戏能风靡全国、历久弥新的魅力正在于此。
姚金成:河南戏曲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传统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原戏曲在充分发挥传统剧目和新编古装剧审美功能、社会功能的同时,对现代生活进行了热切的关注、提炼、开掘、表现,使河南的戏曲创作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除了《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卷席筒》、《七品芝麻官》、《收姜维》、《诸葛亮吊孝》、《风流才子》、《程婴救孤》等传统戏和新编古装剧为河南赢得全国性的荣誉外,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和轰动效应的现代戏。
上世纪50年代的《朝阳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60年代的《人欢马叫》、《李双双》、《扒瓜园》,70年代的《山鹰》、《前进路上》,80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小白鞋说媒》、《儿大不由爹》,90年代的《五福临门》、《都市风铃声》、《老子·儿子·弦子》,新世纪的《香魂女》、《铡刀下的红梅》、《村官李天成》等,这些剧目,因其能够自如地表现现实生活,反映时代风貌,吐露人民心声,从纷繁复杂、稍纵即逝的现实生活中,敏锐捕捉到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人格嬗变、价值追求,成为时代生活的见证和沧桑巨变的缩影,成为人们感受时代、感受生活、感受社会的一份鲜活档案。他们为人们增添了一份可供咀嚼的时代记忆,一份可供品味的人生思考,一份生活的感悟。如此“贴身”的戏曲,怎能让老观众不留恋,新观众不喜欢?
刘景亮(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剧理论家):美善统一,惩恶扬善,明确的道德判断,为所有地方戏所共有,似乎说不上是豫剧的特征。在任何剧种的剧目中都可以找到不计其数的以惩恶扬善来感染、教育观众的剧目。然而认真考察起来,在这一点上,豫剧是个“激进派”。大量的豫剧剧目,善恶分明,冲突尖锐,有炽热的情感倾向。在一些与其他剧种所共有的剧目中,豫剧所表现出的善恶观念也更为强烈。比如《目连救母》,在南方的一些剧种中,目连之母刘氏,确有恶行,打僧骂道,虐待仆人。而豫剧中的刘氏并无任何不善之举。阎罗王将其拿进阴曹,饱受地狱之苦,乃是一大冤案。豫剧的观众和创作者们,认为只有善者才能得到善者的援救,恶者只能受到惩罚。豫剧改编移植一些善恶观念稍显模糊的剧目,往往会在实践中碰壁。
谁说女子不如男
——名家辈出扛鼎中原戏曲
如果说中原戏曲是一座花园,那是因为里面盛开着一株株艳丽的奇葩;如果说中原戏曲的天空很耀眼,那是因为上面闪耀着一颗颗璀璨的明星。中原戏曲的繁荣兴旺,正是由于一代代具有深厚艺术功力、卓越艺术才华、执著奉献精神,享有崇高威望的表演艺术家。每个年代,每个剧种,都不乏扬旗扛鼎的艺术大家,老一代的如豫剧名旦六大家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桑振君,以及唐喜成、牛得草、李斯忠,曲剧的张新芳、马骐、海连池,越调的申凤梅、毛爱莲,四平调的拜金荣等,中年一代的张宝英、王希玲、虎美玲等,青年一带的汪荃珍、李金枝、王惠、李树建等。可谓人才辈出,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采和卓越建树,使河南戏名扬四海、声震九州,并因个人魅力形成了强有力的磁场,吸引着众多观众的心。
石磊:20世纪之前,女演员是登不了台的。20世纪初,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女演员开始登台。这给河南的戏曲舞台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表演、唱腔风格从昔日的粗枝大叶逐渐向细腻典雅转化,把河南戏曲带入了迥异于以往的审美境界。新中国成立后,她们继续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她们的代表剧目如《花木兰》、《穆桂英挂帅》、《陈三两爬堂》、《风雪配》等还被搬上银幕,使中原戏曲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大师是豫剧第一代坤伶中的佼佼者。她从艺的70余年间,练就一副好嗓,集浑身绝技,文武生旦不挡,唱念做打俱佳;熔“豫西”“祥符”于一炉,创“常派”艺术之新腔,苍劲中不失俊秀,粗犷中流露柔美,奔放里见含蓄,娴静又微隐俏皮。这种声腔艺术,曾倾倒豫剧几代演员,一时形成“家家‘刘大哥’(《花木兰》)、户户‘尊姑娘’(《拷红》)”、“十腔九常”的局面,把豫剧旦行的声腔艺术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奠定了现当代豫剧旦行声腔艺术的基础。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常香玉”成了豫剧的代名词。她一生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有105部之多,为观众塑造了花木兰、白素贞、红娘、黄桂英、穆桂英、佘太君、杜十娘、秦雪梅、秦香莲、胡凤莲及母亲、拴保娘等数以百计的艺术形象。这些人物,个个鲜活生动,家喻户晓,深为广大观众所喜爱,都是豫剧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可以说,奠定现当代豫剧旦行声腔基础的人是她;把豫剧艺术推向全国、传播到世界的人是她;使豫剧艺术梆弦不辍、薪火相传的人还是她。从某种角度上讲,豫剧是她,她是豫剧。
马金凤(豫剧表演艺术家):我6岁学艺,7岁登台,如今我照样能登台演出。我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好,嗓子好,没啥毛病,明年奥运会,我才86岁,凭我的身体,到时候完全能再挂帅出征。
看到“豫剧六大名旦画传”出版,我很激动。1980年全省举行流派艺术会演,我们几个姐妹同台表演,讨论笑谈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只要我能唱,我就不会离开舞台。现在,趁我能唱能说能教,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才,一个个超过我们这帮老姐妹,使河南戏曲后继有人。我认为艺术学校要从思想上解决专业课重要文化课不重要的倾向。搞艺术想要高层次、高水平,没有文化素质是不行的。
石磊:“河南梅兰芳”、“豫剧皇后”“河南梆子大王”这三项桂冠,足以昭示在陈素真豫剧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有人说陈素真的唱腔古朴典雅,韵味纯正而又醇厚,是豫剧祥符调声腔的集大成者;有人评价陈素真的做派端庄含蓄,准确细腻又层次分明等,这些评论均不为过。然而我以为“陈派”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流派的要点,就是她的文化品位。同样的祥符调,一经陈大师的口中吐出,就内涵丰富,别具韵味。也就是说,祥符调培育了她,她提升了祥符调的艺术品位。她和同时代的豫剧改革先驱樊粹庭是推动和完成豫剧祥符调文化转型的杰出代表,经过他们的努力,又粗又土的祥符调逐渐变为高尚的文化娱乐。现在的演员要学陈素真,不仅学她的唱腔,更要学习她坚定的艺术信仰和追求。
范红娟:豫剧大师中,我对专唱“哭戏”的崔兰田印象比较深刻,她类似京剧的程砚秋。其悲剧主角如秦香莲、窦氏、秦雪梅、陈杏元、崔金定、柳迎春、陈三两、姜桂枝都是喝黄河水,吃五谷杂粮的具体的人,表达的是黄河边上的中国人的思想感情、精神寄托,所以即使是年代久远,我们也毫无隔世之感。被陈世美抛弃的秦香莲,面对亡夫撕肝裂肺哭啕的窦氏,在现代社会还隐约可见。这些悲剧人物所表现的是普通人的情感,她们的不幸遭遇使我们相信,这些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能够引发我们的共鸣。
姚金成:“看了常香玉的戏,一辈子不生气”;“卖了牲口押了套,也要看狗妞的《三上轿》”;“三天不吃盐,也要看崔兰田”;“少串一趟亲,也要看看桑振君”等等,观众打心眼里喜欢他们心中的“明星”,除了那种狂热的追捧,更不惜用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过分、很夸张的言语来表达他们对心中明星的崇拜。几乎每一位杰出艺术家,都有一帮痴情的观众在追随,不少观众和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之间,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带有“一种生命密码的聚集和传达”(余秋雨语),让他们如痴似狂,魂牵梦绕。而河南戏,正是在这一股股的追星“狂潮”中,聚拢着旺盛的人气,保持着激情和活力。
来源: 河南日报